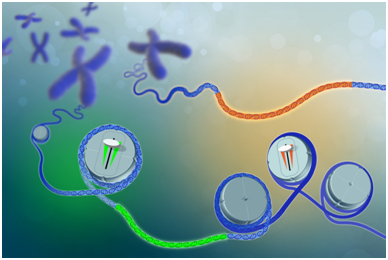出现下一个“罗一笑”你还会转发捐款吗?
(原标题:“罗尔事件”注定成为互联网慈善的标志性案例)

罗一笑的父亲罗尔。 东方IC图
11月30日清晨,《罗一笑,你给我站住》一文刷爆微信朋友圈。父亲罗尔以别致的“卖文救女”新方式为罹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一笑进行网络求助,获取同情与打赏无数。但是很快,反转、辟谣、反辟谣轮番上演,“真相”屡获刷新,目前核心事实已基本清晰——罗一笑的确在今年9月罹患了白血病;重症室的治疗费用,的确动辄每天上万元,但医保的支付比率并不低,截止11月底自付费用仅3.6万元;罗尔目前收入只有4000元/月,但他在深圳和东莞共有3套房产,其自称其中2套没有房产证;30日深夜微信承认打赏系统有bug,宣布冻结相关打赏,12月1日罗尔宣布要建立白血病基金,1号傍晚微信宣布把260余万打赏全部退回。
可以预见,“罗尔事件”注定成为互联网慈善的一个标志性案例。此番舆论关注聚焦的主要有: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到了什么地步才可以向社会求助?求助人又该向捐赠人尽到哪些告知义务?“朋友圈慈善”这种新型慈善类型应该如何得到监督?
今年9月1日施行的《慈善法》规定,开展公开募捐应该制定募捐方案(包括募捐目的、受益人、募得款物用途、募捐成本、剩余财产的处理等)。而深圳市民政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“网友微信打赏行为不算是募捐行为”。也就是说,大家给罗一笑“捐款”,却不归《慈善法》管,钱款的额度和去向,也不受严格监督。
凤凰网发表评论文章《罗尔还谈不上诈骗,但挤占了生命通道》指出,“个人求助”的问题在于,既得不到正规慈善机构的组织支持,也不受到慈善机构的监督、管理,受助人真实性、善款的额度和具体用途,都缺乏透明的披露和有效监督。于是这就变成一场苦情戏的竞技场,看谁的文采最好,谁的故事最催泪。
罗尔的错误在于,没有客观地表述自己的财产情况和真实的医疗费用支付比例。正如网友的归谬:“很多买不起房的网友,在给有三套房的爸爸捐款”。作者沈彬认为“用自己女儿的悲情故事,向不特定的公众拿了钱,需要承担更严格的道德约束……可能罗尔每月的收入不高,不动产一时难以变现,但是,罗尔的确不是那个最最应该得到公众帮助的人,他挤占了生命通道”,罗尔不该利用自己的文才以及媒体界的资源,这么做是在透支慈善的公信力。
微信公号“冰川思想库”连发两文评论此事。作者魏英杰在《带血的营销与嗜血的看客》一文中指出,此间的矛盾在于:罗尔这方与转发、赞赏者之间,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——一方是按照公司公益活动的节奏走,另一方则把这当作是社会募捐,结果活动到后来完全失控,罗尔等人被逼进了死胡同。
此事还让魏英杰想起11年前的“陈易卖身救母事件”,陈易也是被人指责一边接受捐款,一边穿高档运动鞋、戴500多块钱的隐形眼镜以及用手机加小灵通,引来一片骂名。还有人指责,陈易隐瞒了母亲是公务员、有医保的事实。但后来人们又了解到,所谓高档运动鞋是陈易母亲在她上大学的时候买的,已经穿了三年了。而陈易母亲是公务员不假,但医疗费用只能部分报销,需要社会救助并未夸大事实。但在一片网络质疑声中,陈易母亲在愤懑与担忧中死于手术台。
作者认为,在没有用尽自身资源的情况下,罗尔的做法确实操之过急,“但因为事情没有按照有些人所想象的悲情剧演绎,就指责罗尔的做法是‘带血的营销’,拿自己女儿欺骗公众感情,这未免有失公允与厚道。”
“冰川思想库”的另一篇评论题为《对一个网络乞丐,为何一定要把他打翻在地才解恨?》,作者任大刚把罗尔的行为看作一种网络行乞:罗尔没有向谁强制索取钱财,也没有向打赏者许诺任何好处以引诱人上当受骗,而只是一种个人求助,与街头上不停地向不特定人群磕头的乞丐相比,没有什么本质区别;他也像绝大多数真假乞丐一样,程度不同地撒谎,隐瞒部分真相,放大自己的无能为力,以博取最大可能的同情;就像一切乞丐一样,他也有自己具体的“苦情”——女儿罗一笑的确罹患了花费不菲的白血病。
为什么我们能容忍线下乞丐,而不能容忍网络行乞?任大刚认为原因主要在于,网络甄别人真实身份的功能实在太强大,极短时间内罗尔就被迅速“人肉”现出原形,人们受不了这个反转。此外,公众的愤怒,还在于他的财富还涉及高度敏感的、具有意识形态符号一般的“房子”——一个在一线城市拥有三套房产的人,反而被在这些城市奋斗而没有房子的人“捐助”,这比“杀贫济富”还要过分。
作者指出,真正的行乞,就是一种个人向社会求助的行为,他人愿意帮忙就帮忙,不愿意也不应受到指责。“这种行为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,不应受到任何干预。社会需要一些灰色地带,掩藏那些说不清道不明,也不足为外人道的人和事。同样,善心的献出,很多时候需要彼此意会,不需要言明,不需要坚硬的制度保驾护航。他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任,哪怕一不小心轻微上当,一笑置之即可,而不必提着他的领口,怒气冲冲挥舞拳头。”
网络红人和评论员十年砍柴同样认为,转发了罗尔求助文章甚至捐了钱的人也不必太愤怒,亦不必夸大这件事对慈善事业的负面作用。“就如在过街天桥上遇到一位乞讨的人,他面前铺着一张纸书写遭遇之惨,你可以选择不相信;如果选择相信,献出自己的爱心捐了些钱,即使被骗也不用懊恼。你获得了“行善”而带来的愉悦感,自我的道德水准也因此有小小的升华。世上利用公众的爱心的骗局常有,被揭穿了是个好事,吃一堑长一智,公众或许对这类微信上的求援信多一个心眼。但只要建立起权威的调查、甄别机制,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,我相信公众的爱心依然会滔滔不绝,只是降低被浪费的可能心。”
澎湃新闻的评论文章《罗一笑事件:网络上的“虚拟参与”加大了社会的疏离感》,分析视角另辟蹊径。作者刘昕亭关注的是:为什么社交网络上的事件能调动公众如此强烈的情绪?她认为这种虚拟参与感背后所透露的满足感,是一种通过别人而获得的自我满足。

关注本网官方微信 随时订阅权威资讯